坐
2019.12.09
在过去,坐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有人因“坐”得福,也有人因“坐”险些家破人亡。
君臣,夫妻,又或主宾,无论是哪种人际关系,都要在坐的形式、仪态和方向等方面,遵循一定的规则。
坐是一个象征行为,坐具是一种社交媒介。在“坐”上,我们的每一个微妙举止,都意味深长。
早期的中国是没有椅子的,我们现在所说的椅子,其实是西域的舶来品。
两千多年前,孔子开坛讲学,弟子三千,坐而论道。这里的坐,就是大家一同坐在铺着草席的地上。孔子尊崇周礼,他说,“席不正,不坐。”.jpeg) 《杏坛讲学》
《杏坛讲学》
以前的“坐”多为跪坐,重量落在脚踵上,既在物理上节省空间,又是精神上极致的自我约束,是标准的恭谨和臣服之态。甚至到了清朝,皇上在西暖阁召见大臣的时候,大臣一声“跪谢”后依然只能跪在毛毡子上。
和“跪”的恭谨相反,“踞”则是一种岔开腿的坐姿,曾被视为是蛮夷才会有的粗鲁举止。据说孟子有一次撞见妻子这样的坐姿,大怒之下甚至要休妻。
可见那时候的“坐”不是私人行为,而是社交场合中的一种表现形式,在无形中传递着严肃的信息。
为了让“坐”有仪式感,讲求礼仪的周朝用席子定下了一套规矩。
首先是垫几层的讲究。据《礼记·礼器》记载,只有君王屁股下可以坐五层席垫,诸侯三层,其他人根据地位依次削减。
其次还有垫什么的讲究。《周礼·司几筵》中写着,席子分有五种,分别为“莞、藻、次、蒲、熊”。不同的材质代表了不同的等级,铺设给相应的地位的人。
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单薄的草席,无论是在生理需要,还是社会功能上,都无法满足人们进一步的需求,于是就出现了“床”。
别误会,这里的“床”其实是坐具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就有写,“床,安身之几坐也。”
“床”到后来缩小了一些,又被称为“榻”,高度比席高出了20厘米左右,但只是为了将人与湿冷的地面隔开,且可以更方便主人款待和宴请宾客。
虽说坐具变得宽大舒适了,但榻上人们的坐姿依旧是严谨的跪坐。于是就有了“常坐一木榻,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,其榻上当膝处皆穿”的记载,说的是管宁50年来一直规矩地跪坐着,以至于他的坐榻膝盖处被磨穿。
那时候,主人对客人的态度,可以从他的坐具中看出来。楚庄王曾为自己的爱马独设一榻;文帝欣赏慧琳和尚的文采,每次召见都安排独榻给他;而梁国公李岘因为地位低贱,拜见丞相时干脆无榻可坐 。如果不是汉灵帝,中国人可能还会在席和榻之间的选择上犹豫数百年。
据《汉书·五行志》载:“灵帝好胡服、胡帐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饭、胡箜篌、胡笛、胡舞,京都贵戚皆竞为之。”
皇上的喜好就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标,拜汉灵帝所赐,他让胡床传入中原,风靡神州。
但胡床并非床,甚至连椅子都不算,它只是一种交叉的可以折叠的小凳子,类似于今天北方的马扎儿。它方便易携,最早出现在战场上,是君主才能享受到的坐具。
《艺文类聚》有记载,曹操和西凉大将马超打仗,被马超突袭,曹操显得很从容,马超军赶来了,他“犹、坐胡床不起”。
这个小凳子,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交椅的前身。它是中国人从席地而坐变为垂足而坐的转折点,也是坐具革命的起点。
之后的魏晋时期,因人们崇尚率性风流的名仕风度,正襟危坐的坐姿地位也受到了动摇。
.jpeg)
(两个人相对)
(土,土炕),表示两人在土炕上盘腿相对。有的篆文
将两人相对的形象
写成“卯”
(“畱”的略写),表示主人挽留客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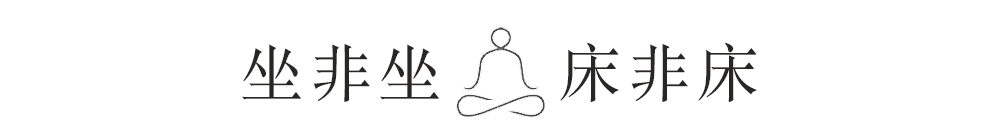
.jpeg) 《杏坛讲学》
《杏坛讲学》.jpeg)
.jpeg)
.jpeg)
.jpe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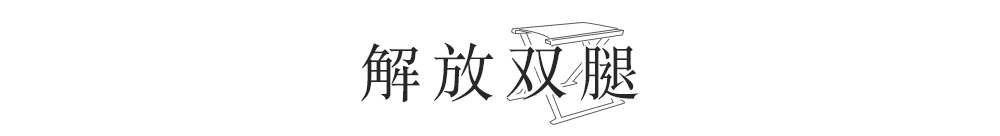
.jpeg)
.jpeg)
.jpeg)
(两个人相对)
(土,土炕),表示两人在土炕上盘腿相对。有的篆文
将两人相对的形象
写成“卯”
(“畱”的略写),表示主人挽留客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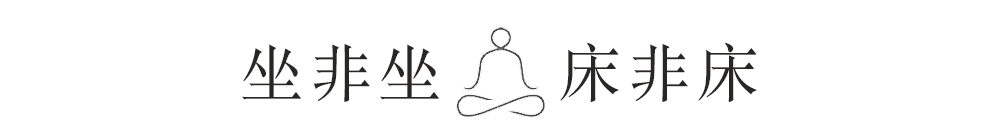
.jpeg) 《杏坛讲学》
《杏坛讲学》.jpeg)
.jpeg)
.jpeg)
.jpe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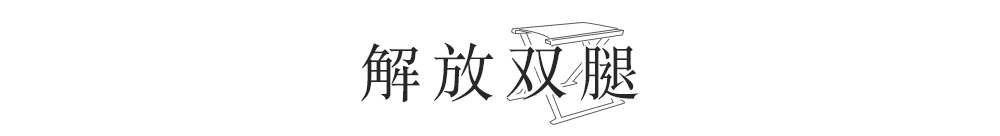
.jpeg)
.jpeg)